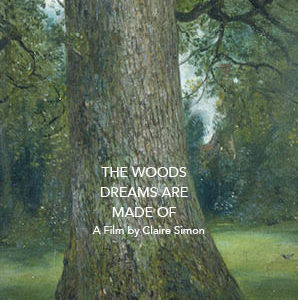白先勇1983年的小說孽子曾描述當年的新公園,是「我們的黑暗王國」,在每夜的公園大門上鎖後,這距離都會區只有一道牆的空間,剎那間會變成一個想像中伊甸園,在這裏我們可以實現真實生活中想也不敢想的夢想。Claire Simon 的紀錄片《森林中的伊甸園》(The Woods Dreams are Made of)以鏡頭和採訪探索Simon所遇到的「一個易進入的『失樂園』」,一個日各種夢想與生活駐足的都會森林,更提供了觀看者一個機會重新思考都會空間與其主體性之間的互動過程。
在Simon的影片中,巴黎文森森林公園彷如一位心胸宏大量但莫名其妙的人物,而它之所以如此包容萬象,除了源於它隨著四季更迭,展露出無窮的景色外,抑有著一種有善的性格——無條件接受每一位在公園中停留的人們。進入森林公園你會遇發現一位疲憊的褓姆,周旋在打盹與照顧嬰兒之間,一位從不放棄的單車族(以及一直想要「表現」給單車族看的曝露狂): 文森森林公園歡迎每一個人。一位居住森林公園的阿嬤聲稱她是為了個人自由來,在影片中她描述了如何在期望孫子錢來拜訪的同時躲避社福機構的同時教一方面期望孫子過來拜訪,為了預備她的孫子過來拜訪,她需要隨時保持警戒,以免公園的巡邏人員會將隨地紮營的帳篷拆除。
此外,還有人為了工作或挑戰而來,性工作者在樹林中等待客戶,釣魚客炫耀和放生他們釣到的魚,初來乍到的居民也到此慶祝,有人運動、有人休息,對生活在這都市的群眾來說,文森森林公園雖建設於都市內,但公園在眾人心中的價值卻是幅員遼闊。即便文森公園被作為性交易場所,依舊不影響的是它作為人們心中理想的伊甸園,文森公園歸屬於都會的生活圈之內,抑又是都會的「異托邦」。森林公園像其他「異托邦」一般,作為一個真實存在的空間,我們在公園中逃避現實生活,卻也同時藉由公園試圖重建一個理想中的生活樣貌,面對公園對於參與者的價值,以及都會設施中所反應出的空間與階級,它到底是被規劃的樂園,抑或是它是否真能公園能作為我們逃離都市生活的「異托邦」?在我們得到答案之前,不如先將這些層層堆起的疑問,默默地留在森林公園中被雪覆蓋的小徑之下,盡情地像那單車族和曝露狂一樣等待新春。
文森森林公園是影片的主角,但Simon藉由採訪作為拍攝的方法,透過每一位受訪者描述他們跟公園之間的關係,說明了公園如何在無形之中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就算鏡頭不離開公園,觀眾依然能參與受訪者的日常生活,此外,有人在公園短暫停留, 在充電或抱持焦慮的情況下,繼續走入公園外頭的真實世界。透過紀錄公園一年四季的變化,以及不同受訪者的故事,影片也讓我們了解森林公園的過去與衰弱,文森森林公園之所以會被視為一座「烏托邦」並不只是因為它是一處公共空間,在過去它曾繁榮於作為軍事基地以及大學校園,但在無人維護之下,公園則逐漸沒落成為林地。
當Simon在影片如此提問,他給我們更多的想像空間,讓我們更廣泛得思考都市空間。如果您有一點年紀,就可能記得228和平公園當時稱為新公園,說不定也會記得白先勇得「黑暗王國」。二二八和平公園蓮花池旁當今每晚有水舞燈光秀,之前,1960年代至1990年代,這裏卻是一個隱密(不過眾人所知)的同志聚集場所,自1996立紀念碑,圍牆被拆掉,還有燈光、等設備,都讓二二八和平公園更接近市民生活,當我們欣賞這些公共資源時,我們該質疑的是在這改名的過程中,有多少的歷史會就此塵封,甚至消逝?如果地方(place)是社會實踐對象,我們也可以跟Simon所拍到的公園裡找砲友的同志一樣,當社交APP代替了公園裡散步、觀看、等待的實踐,我們失去了哪一些人跟人,跟自然,跟地方的關係?二二八和平公園裡應不應該紀念當時的隱晦的生活?一個為LGBTQ政策進步而自豪的台灣,是否有意願記得與承認當時的「黑暗王國」?
《森林中的伊甸園》啟發我們討論都市綠色空間,也讓我們重新面對台灣的公園,曾經是眷村或其他被遺忘的社區。文森森林公園的歷史跟台北不太一樣,不過看完了影片我們可能會想要進一步了解台灣公園的設施背後的空間改建、再利用,與開發。我們所看到的台北,是都市計畫,消費,房地產業,休閒,等實踐構造,這些實踐有何特色?我們還能在台灣的大都會中找到Simon所描述的自由?而這種自由有何代價?我們是否用曾經居住大安森林公園、等都市綠地居民的邊緣化,換來我們都市綠地?這些問題,不是為了懷疑公園的價值,反而,Simon 的影片鼓勵我們去了解我們在追求更開放、綠色的都會時,如何在不同價值尋找平衡。
除了提問以外,這篇充滿詩意,多元聲音的影片也歡迎我們跟森林一起入夢,《森林中的伊甸園》讓我們細膩地欣賞都市生活多元巧合作為幽默,激起了我們對在大安森林公園中夜跑,以及在二二八和平公園打太極的民眾的好奇心,看了影片以後,我們會更珍惜這些僅有的都市綠地。更重要的是,我們跟文森森林公園的人們有著共通的夢想——一個有雅量的,讓每一個市民都有棲息之地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