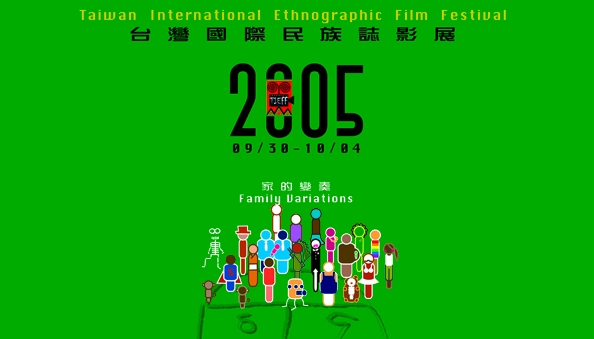胡台麗
(本文刊登於9/24之聯合報副刊)
「每一個人都在尋找一個甜蜜的家,我何嘗不是?」
原住民歌者胡德夫(kimbo)在公視原住民記者哈露谷與嘎喇拍攝的紀錄片《kimbo匆匆》中說出這句話。聽到現實生活中遭遇許多挫折的老友胡德夫的表白,不知怎地,我有激動想落淚的感覺。
「家」是人類社會揮之不去的基本單位。一夫一妻結婚生子是最普遍的「家」的概念,可是放眼世界,「家」的面貌繽紛雜陳,不斷挑戰我們對於「家」的刻板印象。繼2001「島嶼聯線」、2003「遷徙故事」,今年度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以「家的變奏」為主題,透過來自不同地區的影片,讓大家體嚐「家」的各種滋味,並沈思「家」的存在意義。以下我僅挑選部份影片來顯現「家的變奏」。
◎ 狩獵採集與畜牧多妻之家
民族誌影片攝製史中極重要而動人的「家」與「家」的接觸發生於1951年。那年,美國波斯頓的馬歇爾家庭來到西南非的喀拉哈里沙漠,和靠狩獵採集方式維生的灌叢人(bushman)奧瑪家庭共處。兒子約翰‧馬歇爾才18歲,拿著父親給他的一部電影攝影機,開始紀錄這個被視為極為原始與神秘的族群,並學會了該族語言。1958年約翰被南非政府限制入境,一直到1978年才與奧瑪家族重聚。此時,灌叢人的原居地大都被政府據有,已全部遷到瓊貴地區,脫離了狩獵採集生活。約翰‧馬歇爾的攝影機繼續紀錄奧瑪家族的生活,終於於2002年完成了五部「喀拉哈里家庭」影片,呈現了長達半世紀的變遷。今年4月22日,約翰‧馬歇爾因肺癌去世,民族誌影展特選其中兩部和早期拍攝的《愛,開玩笑》放映以為紀念。
以「一夫多妻」為通則的社會是如何運作的?大衛‧馬杜格和其妻茱蒂斯‧馬杜格是一對著名的民族誌紀錄片工作者。他們的鏡頭帶我們進入東非以畜牧為主的圖爾卡納族「一夫多妻」家庭。有位受訪者在「我和我先生的太太們」影片中神色自若地說道:「我們通常有五個老婆。如果只有一個老婆,不算是結了婚,會被譏笑為單陰道的沒用男人」。又聽到婦女抱怨:「要看管駱駝,就管不著羊;要看管羊,就顧不了駱駝。誰來造圍籬?誰來給牠們喝水?」她們便主動地為丈夫尋找更多妻子來分攤工作。
◎ 跨性與同性之家
對於那些無法認同依照生理性徵劃分男女的人來說,與異性結婚成家是很痛苦的事。在巴基斯坦的回教世界裡有一小群生理上的「他」自認是女人,無論是裝扮或與舉止都與女人無異,並且集結成家,再連成社群。在《我的美麗與哀愁:巴基斯坦的跨性人》一片中,我們便看到這類為文化所接納與尊重的「跨性人之家」。家中有一較年長者為「母親」,也扮演「老師」角色,但家中成員間並無性關係。這些人的主要職業是在生日宴、婚宴等場合跳舞,將歡樂與祝福帶給人們。
陳俊志的《無偶之家往事之城》則處處奔流著男同志期盼共組家庭卻因愛人喪生而無法圓夢的哀慟。阿龍在片中對已逝伴侶阿煙的姊妹說:「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妳們,能夠接受我。我接觸到妳們這個家庭之後,我感覺非常地溫馨。」未亡者彼此接納、融為一家的結局既甜蜜又辛酸。
男同志成「家」後能生孩子嗎?《父性本能》一片提供了一個鮮活有趣的實例。馬克和艾瑞克這對愛侶在電腦網路上徵求「代理孕母」。他們以將精子注入女體的方法,雇請代理孕母先與馬克生一女,再與艾瑞克生了次女。雖然圓了夢,但這樣的生育方式與家庭組成會衍生怎樣的倫理與法律問題?
◎ 傷痕與特異之家
今年民族誌影展入選的影片中最讓我刺痛難忘的是《我親愛的孩子》。片中出現許多家庭照片,但是父親的臉永遠被切除在鏡框外。沒有臉的父親是女兒從小烙在身體和心靈上最深的傷痕。家暴和亂倫悲劇導致一場弒父官司。這部挪威紀錄片以含蓄精妙的手法將傷痕掀開,讓我們直視「家」的陰暗面。
「家」也會因不同族群接觸而受傷。《是誰殺了塔克雅?》一片敘述的是一位澳洲原住民領袖在自己領地上殺了一位白人警察,結果被監禁和在法庭中受審,最後不知所終。此事件讓他的家族受到很深的傷害,而他的後代也為找不到他的屍骨,以致於無法藉傳統喪葬儀式將亡魂的力量與智慧留給族人而焦慮不安。70年後,原住民和白人兩個家族尋找和解之道。
未成年的少女懷孕生子後,「家」在何處?從一部紀錄小媽媽的尼加拉瓜影片《少女媽媽》,我們可以看到青澀的小媽媽和小爸爸在面對新生命時的無知與徬徨。影片最後打出字幕:「在尼加拉瓜平均每天有400個新生命誕生,其中有100個小孩的媽媽是未成年少女」。
《綁架新娘》和《黑猩猩之家》是兩部題材相當特異的影片。位於中蘇邊境的吉爾吉斯鄉下,至今仍有三分之一女子被綁架成婚。片中女子說:「綁架、接受、活著,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會慢慢去適應彼此,愛會隨著時間增長」。一對美國夫妻收養了兩隻黑猩猩。在《黑猩猩之家》片中,妻子說:「儘管我們都明白黑猩猩非常難以預測,飼養牠們很冒險,因為牠們很強壯,屬於野生動物,有能力殺死我們。但我仍舊強烈感受到,牠們擁有愛和情感,絕不會攻擊我。」黑猩猩與牠們「父母」相處的情形真是突梯滑稽、匪夷所思。
◎ 移民與安寧之家
台灣這個島嶼上不斷產生原居民與外來移民結婚形成的家。吳平海在《謝婷與她的歌》和《飄洋過海的家》中紀錄了晚近嫁到台灣的大陸新娘和外籍新娘。嫁到美濃農家的謝婷說:「我說嫁過來了,自己有家庭了,應該要面對啊,要去吃苦啊,不可能一嫁過來就來享福,我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永和社區大學進修的外籍新娘表示:「最大的困難就是我們來這邊的時候,跟婆婆等家人沒辦法溝通,每天在家裡一直哭」。移民面臨的是適應問題,以及原家和新家的情感糾葛。《石頭夢》影片中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老榮民劉必稼,在妻子過世後吵著要回大陸。無血緣關係的繼女極力慰留:「他一直想說他要回去那邊定居啊!這邊也是他的家!我是不同意他回去那邊。兒女都是在這裡,你回去一個老人家在那裡,我們哪放心?」情真意摯,令人動容。
《陪我走一段》描述的是荷蘭阿姆斯特丹一棟為絕症患者佈置的「安寧之家」。與醫院的「安寧病房」不同,「安寧之家」更像「家」,有客廳、餐廳、寬敞溫馨的廚房,和與日間經常來訪的家人舒適共處的空間,而醫生、護士、義工就在不遠處,可獲得方便的照護。像這類可減輕病患家屬與病人在自家朝夕共處壓力的「安寧之家」的設計,可以讓我們更深刻思索「家」的意義。
◎ 拍攝自己的家
民族誌影展開幕和閉幕各有一部由孫女拍攝阿媽的影片。紀錄片導演將鏡頭對準自家人時很容易陷於細節,但這兩部片子都透過家族和個人的故事,展現出宏觀的視野。《62年與6500哩之間》是自幼移民美國的張文馨返回台灣攝製的紀錄作品。她的阿姨代年近百歲的母親寫了一本自傳,記述她經歷的時代變遷和對民主的追求。導演藉著過去拍攝的阿媽影像、配合自傳和母親與已中風不能說話的阿媽的溝通,探索一個女人、一個家庭與台灣歷史的交錯,也在追尋她個人的家國認同。我們看到阿媽以抖顫的手寫下「平安」兩字,這是她對台灣最深的期盼。
《永遠為你》是一則戰亂中譜出的家庭羅曼史。導演找到一小段祖母年輕時的電影毛片。祖母永遠神采飛揚地述說著戀愛史:「那時我遇到了妳的祖父,深深愛上他,我的命運就此註定」。但在二次大戰期間,長子出世前,祖父參加勞動營後竟然失蹤了。孫女導演從實地查訪的蛛絲馬跡中推測祖父可能在印度孟買居住過。祖母不願接受任何可能被先生拋棄的假設,堅持著她對丈夫的愛與信任。在祖母的心中,記憶遠比現實更珍貴。「家,甜蜜的家」的意象不容戳破。事實上,影展中所有的「家的變奏」都譜出相同的對於愛與美滿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