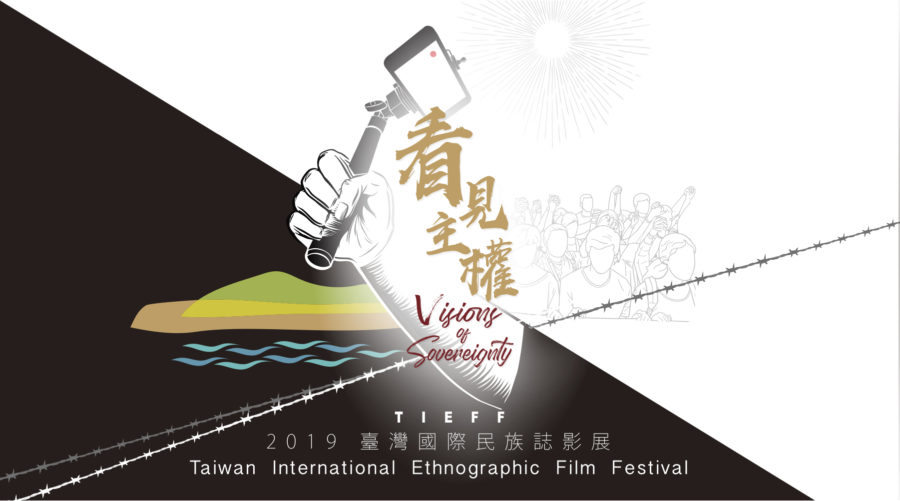今年四月,紐西蘭電影界失去了一位傳奇人物:毛利演員Anzac Wallace(1943-2019)。Wallace年輕時誤入歧途,從竊盜開始幹起,最後因搶劫案入獄,三十歲才被放出來,之後因飾演紐西蘭電影《復仇》(Utu,1983)的主角而舉世聞名。《復仇》一直都有紐西蘭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之雅號,揭開了1870年英國殖民政府的軍隊、前來開墾的平民、還有在軍中擔任嚮導的毛利人與族人之間衝突與血仇的黑暗歷史,對80年代宣稱族群和諧的紐西蘭社會是很大的衝擊。如此大格局的電影,為何會找一位過去從來沒有電影拍攝經驗的素人Wallace擔當主角的大任呢?出獄後,Wallace在奧克蘭Mangere大橋興建工地工作,1978年在他的領導下,建橋工人因不合理的遣散發動抗爭,是紐西蘭工人運動史上重大的事件。這整個事件被當時一位紐西蘭新銳導演捕捉下來,製作成《橋:一個紛爭中的人的故事》(The Bridge – A Story of Men in Dispute,1982)這部紀錄片,並找來Wallace擔任旁白。他在抗爭中不妥協的立場與紀錄片中沈穩的聲音,吸引了《復仇》導演Geoff Murphy的注意,決定邀請他飾演片中原本是英軍嚮導但因村落被軍方屠殺而踏上復仇之路的毛利勇士一角。而那位敏銳識才的紀錄片導演,則是這次民族影展開幕片《梅拉塔:母親的解殖電影》的焦點人物:紐西蘭毛利女性導演Merata Mita(1942-2010)。
Mita是紐西蘭毛利電影工作者的先驅之一(另一位是Barry Barclay,1944-2008),也啟發了80年代後世界原住民電影的發展。然而身為一位毛利女性和母親,這條路走來是更加艱辛-她有來自三段不同關係的六個孩子(其中一段是與《復仇》導演Geoff Murphy,兩人的孩子Heperi Mita就是《母親的解殖電影》的導演),並且曾違背己願成為家庭主婦、體驗離婚後親人的背棄、遭受家暴與種族性別歧視、獨自在都市中身兼多份工作撫養孩子。或許正是這些生命經驗,讓她能更犀利地觀察到毛利人,特別是女性,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她最早的紀錄片作品即是針對使命灣巴斯辰角(Bastion Point)抗爭事件的《使命灣:第507天》(Bastion Point: Day 507,1980,本屆民族誌影展也有放映)。巴斯辰角是為紐西蘭軍方長期佔領的毛利土地,1976年政府決定將之轉型成高級住宅區,隔年這塊土地的傳統擁有者Mgati Whatua部落族人發動長期佔據抗爭運動,在上面建造房舍與田地。1978年五月,政府出動警察與軍隊將抗爭族人團團包圍強行驅離。Mita全程側拍紀錄,並捕捉到在以往公眾抗爭中不常出現的毛利女性長者身影。
她的母親身份也讓她體悟到原住民電影的創作基礎,也就是社群的工作精神。怎麼說呢?當她開始學習拍攝影片時,她已是一群孩子的媽,而這些孩子也會跟著她一同工作、前往不同拍攝地點、幫忙搬運器材、甚至入鏡。他們就是Mita的「社群」,有時是她的負擔,但也是最忠實的支持者,與她一同吃苦也共享喜悅。拍攝原住民電影也是如此,專業與在地社群的界線很多時候是相當模糊的,無法清楚切割,但在此之中關係則是長久的。這樣的關係也能一再地提醒拍攝者,作品是關於整個社群,他們的各個面向,而非梳理乾淨塑造給特定觀眾。她的兒子Heperi在《母親的解殖電影》中訪問他的哥哥Bob時,哥哥的孩子突然奔入鏡頭打擾到訪談,但鏡頭始終沒有中斷,捕捉了到家人的真切互動,相當程度反映了Mita所說的「社群」創作精神。當今紐西蘭知名的毛利導演Taika Waititi則提到,當他在構思《我的爸爸是麥可》(Boy,2010)的劇本時,原本的內容與當時多數毛利主題電影無異,充滿陰鬱悲傷的氣氛,但在與Mita聊過後,他受到啟發加入了早已在日常生活中親身感受到的毛利式幽默,也讓《我的爸爸是麥可》跳脫窠臼,講出很不一樣的當代毛利故事。
Mita在受訪時表示:「當你有小孩時,你就等於投資了未來。所以你會再次挺身對抗不公不義。」她對孩子的愛,讓他們在顛簸的童年中仍支持著母親,甚至日後拍攝紀錄片來紀念她。她對孩子的愛,讓她能勇敢地挑戰毛利人在紐西蘭社會中諸多未被深刻討論的問題。她對孩子的愛,讓她成為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影像工作者的母親角色,不斷啟發他們。切‧格瓦拉說過:「真正的革命是由深刻的愛意所引導的。」而這種愛,時常是來自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