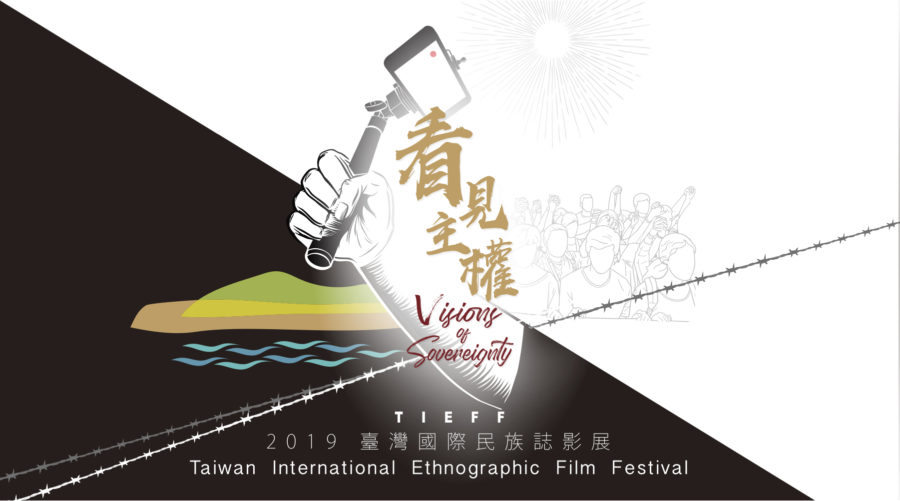在衝突頻繁的地域從事紀錄工作,穿梭於涇渭分明的仇恨中,如何既忠實呈現其高度政治化的面貌、卻不落入二元觀點的陳腔濫調,始終是說故事者的一大挑戰。自1940年代起算,衝突已70多年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吸引了無數帶有問題意識的紀錄者,也使許多有心挑戰傳統論述的人們受傷離去。「兩面不討好」「裡外不是人」是許多記者朋友私下透露的心聲,我亦曾覺得,《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作者、前BBC記者利皮卡・佩拉漢(Lipika Pelham)引述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所言「耶路撒冷是位性愛成癮的老嫗,不斷壓榨一位又一位情人,至死方休,而後一個哈欠便將對方從自己身上抖落」,很適合描繪這塊令我魂牽夢縈、心情複雜的土地。佩拉漢最後也離開了以巴。
在第十屆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看見主權:到底是誰的土地?」單元中,兩部拍攝於這塊土地的紀錄片,故事都圍繞著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境內的以色列屯墾區(settlement)進行,但都在記錄與介入之間,選擇了令人坐立難安的方式,挑戰真相與想像的界線。
以色列屯墾區的歷史或許可追溯至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然而其於人權關注者眼中萬劫不復的負面形象,與40年代以來以色列佔領土地、導致許多流離失所淪為難民──侵略者形象的聯想──脫不了關係。一群無家者獲得家園、導致另一群人淪為無家者的悲歌,早已將以色列國度的存在性蒙上名不正言不順的陰影。而70多年來,無論民情、輿論風向與人們對領土的想像如何變異,以色列隔離牆的建立、佔領區的擴張,加上近年來其軍事屯墾區與私人佔領區(outpost)數量的大肆成長,既是令一國方案(one-state solution)支持者百口莫辯、反映鯨吞蠶食的暴力跡證,也是令眾多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支持者心碎為時已晚的尷尬難題。
在此一邊界模糊、國族認同模糊、身分模糊、情緒模糊的地帶中,所謂家園究竟是否名不正言不順的陰影,也隨著屯墾區的擴張而擴大。這兩部由以色列裔導演執導的紀錄片,用不同的方式,揭開令過去(或許未來亦然)世世代代困惑的家園想像,挖掘政治對立下人與人之間(或各自)壓抑的懸念,也刺激了(自認)懷抱立場的我們。
《一個「叛徒」的死前歲月(Around the Bed of a Dying Collaborator)》故事幾乎就發生在一棟四方屋裡,沒有離開、也離不開。孱弱的巴勒斯坦父親烏納斯不住地表達自己毀了一個家的遺憾。在人生倒數的最終日夜,病榻旁的20架攝影機是他觀察陌生世界的窗──充滿石塊、槍、子彈與綁架的世界,而他懷疑或許是自己親手打造了這樣的世界,才葬送兒子們的成長與未來。然而,即使傷痕累累、遭受性命威脅,兒子們依然選擇留在充滿記憶的家園。
「這房子的味道在我心頭揮之不去……讓他們殺了我,我不會離開的。」
「你是怎麼回事?我沒辦法再照顧你了。」
倒敘憾恨的形成,故事的切入卻是陡峭的視角。當畫面走出房舍,我們聽見希伯來文男聲,描繪著猶太民族政治正確用語裡稱之為朱迪亞—撒馬利亞(Judea and Samaria)、當今普遍被稱為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土地。土地一年一年、一塊一塊被誘騙買賣,有錢你就能買到坐擁死海絕佳風光的房舍──但有比美麗風景更重要的企圖,掮客不會說;甚至,有能力的掮客可讓賣者錯信買者是自己人。
諷刺的是,兒子為撒手人寰的父親預約墓園,最後一刻也恐懼得決定偽造爸爸的名字,讓賣者誤以為逝者另有其人。
家、國、政治的糾葛裡,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的共謀不被原諒,並不難理解。然而,相較於惡有惡報的敘事線,烏納斯臨終前緩緩道出的一段悔恨,令人極度心疼,因為若無買賣土地之汙點,那樣的悔恨便不必存在。而關於此生認識誰、與誰相遇、與誰交好或交惡,或許,許多人在有能力選擇前,命運或環境就已為其決定。兒子們選擇不怪罪父親,忽略邪惡的平庸性,但他們能理解父親童年來不及學習的仇恨,竟成為無顏面對後生的理由嗎?
「我在哪裡?我站哪一邊?那是沒有人想談論的黑暗秘密,如影隨形。」父親離世,鏡頭終於走出老家,起風的山坡卻好似令人透不過氣。憾恨如鬼魅般如影隨形,明明其起源是無法改變的既成事實,造就的卻仍然是無數抬不起頭、必須背負歷史共業的家族及未來世代。
鏡頭前的我,也渴望知道烏納斯所言哪些為真、未露面的口述者是誰、希伯來男聲描繪的歷史時代有哪些與父親從事土地買賣的歲月重疊。「對你我來說是沒有所謂佔領(occupation)的。」烏納斯──身為一位巴勒斯坦人──這句話,在今天聽來,幾乎十分超現實。片尾,壯年時的他甚至在電視機裡慷慨激昂地呼籲巴勒斯坦民眾勿騷擾他的家庭,否則以色列人會來保護他……
相較於烏納斯故事中敘事者線路的隱晦,《在惴惴不安中面對(Unsettling)》導演艾芮絲.札琪(Iris Zaki)則直接以紀錄片做為一種行動,進入西岸屯墾區提哥雅(Tekoa),朝一桌兩椅架設攝影機,擾動了居民也邀請了居民。由於她毫不掩飾自己的左派立場,短短一個月的互動經驗中產生正負面情緒,而故事就發生在札琪的居所、這一桌兩椅,及附近巴勒斯坦人穿梭的檢查哨間。
以色列的屯墾區大多居高臨下,擁有良好視野。當中有些看得到早期人們以集體公社(Kibbutz)構築夢想家園藍圖的影子:自耕自種、清晨瑜珈……片頭的「免費擁抱(Free Hugs)」及提哥雅的喜樂街(Joy Street)、好客街(Hospitality Street)便可嗅見那股氣息──不談論政治,屯墾區也許是很浪漫的地方。我在以色列沙發衝浪(couchsurfing)時有次住進屯墾區,沙發主首先和朋友及我驕傲分享的就是夜景。
然而美妙環境的背後,是土地掠奪的不正義。有趣的是,由於鏡位轉換在札琪與受訪者之間,我們得以看見她面對不同人物、不同對話時的神情與姿態。有時她眼裡發光,有時她顯得無力。札琪立場的鮮明,使得受訪者的搖擺恍如自相矛盾的喃喃自語。
或許確實,仍有許多以色列人在夢境中囈語,而他們確實曾有過美麗夢境。我想起也曾參與過國際民族誌影展的以色列導演暨藝術家塔瑪拉‧厄爾德(Tamara Erde),在《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上映、遭以色列教育部於各級學校禁演後,花費約3年展開另一場更私密的探索──30年代起為錫安主義當局擔任攝影師的外公伊弗拉恩(Ephraim Erde)。她與劇組攝影師、錄音師駕著一輛大篷車公路旅行,將紀錄片融合行為藝術,完成《尋找錫安(Looking For Zion)》
這趟公路旅程中,她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各角落尋找牆面,投影外公鏡頭下的畫面;今日的地景遂成為昨日黑白影像的巨大載體,觸發了許多對話。劇中有一幕,塔瑪拉在以色列與加薩口岸艾雷茲(Erez)旁,將照片投向覆滿鐵絲網的水泥牆面,服役中的年輕以色列國防軍士兵站在一旁好奇觀看。
旅程後的想法?去年在巴黎訪談厄爾德,探問了她的心情,她是這麼說的:
「即使明白影像已經是過去式,且終究無法呈現事實的全貌,但那依然捕捉了很多東西。
我很難過,我們所處的今日,距離外公那時想像的、想透過鏡頭呈現的樣貌,很遙遠。」
廖芸婕 跨國自由記者
「巴勒斯坦之和平與武裝抗爭」攝影系列入圍 2018 年卓越新聞獎。自由工作者,以文字及影像連結國際、臺灣議題,跨國作品散見國內外媒體,曾獲新聞、設計及影展獎項。著《遙遠人聲》、《我們掙扎,築起家園》、《獨行在邊境》等。2017及2018年之間,往返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西岸地區,在兩地蹲點數月。2019年與藝術家洪瑋翎、朱筱琪合作表演式講座《界・現?穿梭在以巴衝突與餐桌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