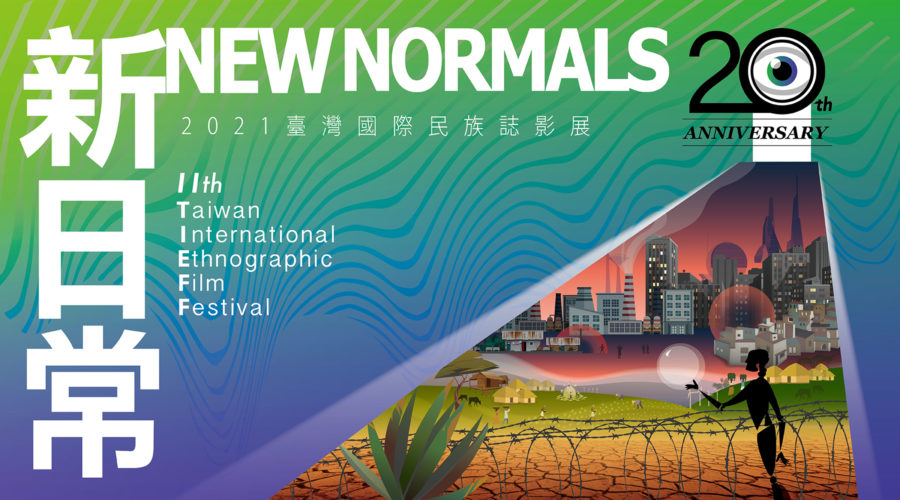提到原住民實驗小學,不少人可能聽聞過泰雅族的博屋瑪國小,但卻未必知道,這幾年陸續有不同族群、區域的原民國小,正以各種美麗的姿態努力在部落生根,繼而發展出別具特色的民族教育。其中,和博屋瑪同時在2016年變身為此領域之先驅的屏東三地門鄉排灣族地磨兒民族實驗小學,正是撒舒優《masan caucau 成為真正的人》這部片所深入描繪的主角。
今年已是撒舒優第三度入選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而這也是我們相識的緣由。2013 年他以探討阿朗壹古道存廢議題的《最後12.8公里》首次獲選,隔年全國巡迴時來暨大放映,此後只要他一有新作,我都迫不急待地邀來暨大分享,包括談核廢料存放的《原來我們不核》(2015)、以部落托育班為主題的《作部落的人》(2016),以及這部探討原住民實驗小學核心價值的新片。
這四部撒舒優的作品,均致力在剖析重要的當代原住民議題。前兩部所處理的是具全國知名度的爭議性話題*,相對於此,後兩部探討原住民教育之紀錄片雖在議題聲量和受關注程度上較為侷限,但在我看來,卻是更貼近原住民社會和導演自身的內在與日常,因此格外需要透過紀錄片做為認識與交流的媒介,讓非原民圈的人能夠理解,進而引發更多的討論與省思。
撒舒優之所以關注原民教育和其身為父親的角色有關。拍攝《成為部落的人》時,他的小孩正是讀部落托育班的年紀;開始動念拍《masan caucau 成為真正的人》,則是因為孩子升上小一,進入地磨兒國小就讀。而這兩部作品的片名如此相似亦非巧合,就如前一部片中的馬躍比吼所言:「那很可惜,我們過去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是我們的教育裡面,就是沒有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魯凱人、排灣人」。不同的文化擁有不同的「人觀」,這是人類學的基本知識,然而在過往獨尊漢文化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裡,原住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所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離部落文化越遠。因此,地磨兒國小的民族教育所要作的便是扭轉這樣的矛盾,讓孩子們能夠真實踩踏在部落的土地上,身體力行地感受、學習自身族群的文化,進而「成為真正的人」(masan caucau)–有排灣族靈魂的人。
在這部紀錄片裡,撒舒優細膩地描繪了三個不同世代族人–傳遞文化知識的長輩(vuvu)、老師和學生家長,以及小學生–在民族實驗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與心情感受。其中特別讓我有感的是年齡和我相近的中生代,這個世代所面臨之文化失根的狀態雖不至於像澳洲「失竊的一代」那樣慘烈,但在過往「同化政策」的強大壓力下,往往徘徊在原與漢、傳統與現代之間被迫做出選擇,是最無所適從也最被拉扯的一代。透過導演的鏡頭,我們看到導師楊萍除了作為長輩和孩子間重要的溝通橋樑之外,面對婚禮這個學習主題時,她特意選擇了自己很陌生的「情柴文化」,就是想要和孩子們一同努力學習。還有片中看到孩子優異表現時激動落淚的葉姓學生家長,雖然在外人眼中擁有相當不錯的學歷和成就,他的心中卻遺憾著沒有能力捍衛自己的文化、為自己文化說話,因此毅然而然地選擇了讓孩子回到部落小學,成為第一屆接受實驗教育的新生。
對於所謂的「民族」「實驗」教育,許多人儘管同意文化的重要性,但總還是有所疑慮。一來是擔心原住民學生會因學「文化」而排擠到一般學習,以致缺少競爭力,二來是害怕孩子從實驗小學畢業之後,依舊必須回到一般教育體制無法適應。撒舒優並沒有在片中直接回答這兩個最常被提出的質問,甚至明白地表達了老師和學生對於後一個問題的不安。「為什麼沒有地磨兒國中呢?」孩子問。
然而,如果細細品味這部片,相信你們會和我一樣,感受到更多的是希望與期待。因為民族實驗教育所要翻轉的不只是過去缺乏原住民文化內涵的教學內容,還有教學與學習的方式。當你在片中看到這些小學生精彩的筆記、感想、小組行動與展現的自信,當你感受到白髮蒼蒼的vuvu看著孩子學習文化時眼中的欣慰,以及孩子們對vuvu發自內心的崇拜和感謝,那麼,對於上述有關民族教育的憂慮,或許會有更多可能的、不同於以往的想像與解答。
*深入剖析可見林文玲(2020)在《中外文學》發表的<社會議題的中介與轉化:以撒舒優.渥巴拉特兩部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為例>一文。